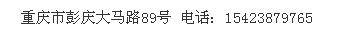
《诗经》第一百零九篇《园有桃》
[作品介绍]
[注释]
[译文]
[赏析1]~~[赏析5】
园有桃
[诗经·国风·魏风]
园有桃,其实之殽。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不知我者,谓我士也骄。彼人是哉,子曰何其?心之忧矣,其谁知之?其谁知之,盖亦勿思!园有棘,其实之食。心之忧矣,聊以行国。不知我者,谓我士也罔极。彼人是哉,子曰何其?心之忧矣,其谁知之?其谁知之,盖亦勿思!
[作品介绍]
《园有桃》,《诗经·魏风》的一篇。全诗二章,每章12句。是1首先秦时期华夏族诗歌。这首诗以4言为主,杂以3言、5言和6言,句法参差,确如姚际恒所说:“诗如行文。”(《诗经通论》)压韵位置两章诗相同,前半六句韵脚在1、2、4、六句末;后半六句换韵,韵脚在7、8、10、11、12句末,并且10、10一两句重复,哀思绵延,确有“长歌当哭”的味道。
[注释]
①之:犹“是”。肴,吃。“其实之肴”,即“肴其实”。
②之:犹“其”。
③歌、谣:曲合乐曰歌,徒歌曰谣,此处皆作动词用。
④是:对。
⑤其:作语助。
⑥盖(hé何):通盍,何不。亦:作语助。
⑦棘:指酸枣。
⑧聊:姑且。行国:离开城邑。“国”与“野”相对,指城邑。
⑨罔极:无极,妄图,没有准则。
[译文]
园中桃树壮,结下桃子鲜可尝。心中真忧闷呀,姑且放声把歌唱。有人对我不了解,说我士人狂妄太骄狂。那人是对还是错?你说我该怎样做?心中真忧闷呀,还有谁能了解我?还有谁能了解我,何必挂念苦思索。
园中枣树直,结下枣子甜可食。心中真忧闷呀,姑且漫步出城池。有人对我不了解,说我士人多变不可恃。那人是对还是错?你说我该怎样做?心中真忧闷呀,还有谁能了解我?还有谁能了解我,何必挂念苦思索。
[赏析1]
这首诗语言极明白,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,但是对诗人“忧”甚么,时人为什么不能理解他的“忧”,反认为他自满、反常,难以找到确切答案。同时他自称“士”,而“士”代表的身份实际其实不肯定,《诗经》中三十三篇有“士”字,共54个,仅毛传、郑笺就有多种解释,如:“士,事也”,指能治其事者;“士,卿士也”;“士者,男子成名之大号也”;“士者,男子之大号也”;“言士者,有德行之称”;“士,军士也”;“他士,犹他人也”等,所以这个自称“士”的诗人是何等角色,很难认定。与之相应,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:《毛诗序》谓“刺时”,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作实为“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,将黜太子申生”;丰坊《诗说》说是“忧国而叹之”;季本《诗说解颐》以为是“贤人怀才而不得用”;牟庭《诗切》以为是“刺没入人田宅也”。今人或说“伤家室之无乐”,或说“叹息知己的难得”,或说“衰败贵族忧贫畏饥”,或说“自悼身世飘零”,或说“反应了爱国思想”,不一而足。《诗经选注》说:“我们从诗本身分析,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,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,是由于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,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,因此他在忧愤没法排解的时候,只得长歌当哭,自慰自解。最后在无可奈何中,他表示‘聊以行国’,置一切不顾了。因此,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,属于明珠暗投的可能性极大。”故指此为“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”。
此诗两章复沓,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;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。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、枣树起兴,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,味美又可饱腹,而自己却无所可用,不能把自己的“才”贡献出来,做一个有用之人。因此引发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,所以3、4句接着说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”,他没法摆脱心中忧闷,只得放声高歌,聊以自慰。《毛诗序》说:“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”这位正是由于歌之不足以泻忧,决定“聊以行国”,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,到别处走一走,看一看。这只是为了排忧,还是想另谋前途,没法测知。但从诗的五六句看,他“行国”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诗云:“不我知者,谓我士也骄(罔极)。”诗人的心态似乎是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。由于他的思想,他的忧愁,特别是他的行动,国人没法理解,因此不免误解,把他有时高歌,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,视为“骄”,视为“罔极”,即反常。诗人感到非常委屈,他为没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,所以7、八两句问道:“彼人是哉?子曰何其?”意思是:他们说得对吗?你说我该怎么办呢?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,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。最后4句:“心之忧矣,其谁知之!其谁知之,盖亦勿思!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,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,因此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,故一再申说“其谁知之”,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。他的期望值其实不高,只是要求时人“理解”罢了,但是这一丁点的希望,在当时来讲也是不可能的,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。全诗给人以“欲说还休”的感觉,风格沉郁顿挫。陈继揆《诗经臆补》认为:“是篇一气6折。自己心事,全在1‘忧’字。唤醒群迷,全在1‘思’字。至其所忧之事,所思之故,则俱在笔墨以外,托兴当中。”
[赏析2]
这是一篇忧时闵国的苦闷悲愁之诗。《诗经百科辞典》说:“这是写一名士人抒发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忧愁,但又不被人们理解的苦闷心情的诗。”
诗歌紧紧围绕一个“忧”,抒发作者心中忧时伤国、苦闷悲愁的忧患意识。诗篇慷慨悲凉,诗情深沉痛切,诗绪一波三折。各章开头均以他物(桃、棘)起兴,言桃、棘可以果腹。引发下文忧时闵国的忧患之词。意思是有桃方能果腹,无桃岂能生存。今国中衮衮诸公,不知衮阙(喻君主的过失),不察民意,不思有备无患之策,不理民生之疾苦,居高位而不尽衮职(古代指三公的职位;亦借指三公),国有患而不知补察时过,浑浑噩噩,自以为是。岂知人民已觉醒,外敌早已觊觎,国无计而民将不生。于此之时,普天之下,仍然食桃食棘,无所忧愁。不知桃、棘将尽,国将不存。我呼之唤之,警之醒之。无奈,忠言逆耳、孤掌难鸣,人微势单,时人以我为多事之人,称我骄罔无极。我忧兮虑兮,歌之谣之,聊以行国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。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?更有甚者,称我狷傲多虑。他们这样说对吗?你们怎样看待这件事情?我的这些忧愁,难道真是杞人忧天?普天之下,有谁能够真正的了解我呢?大概我此生再也不能找到知音了,这样活着,生不如死!既然如此,我还想它干什么?不如来一个大撒把,甚么都不管,甚么都不想。作者就是这样,以抒怀的情势,为我们塑造了一名狷介愤激、忧时伤国的“爱国者”形象。他之所以如此,其一由于他眼光深远,其二由于他对自己祖国爱的深沉。但是,在“举世昏昏”,人无远虑的庸俗国情下。诗中抒怀主人公倍感孤独,大有一种“音单声稀”,独行孤岛的感觉。眼看着民不聊生,国势日落,却无可奈何。只能含着眼泪眼睁睁的伤感魏国这岌岌可危的处境,独自体味“大厦将倾”时的悲痛与忧愁。此所谓“举世皆醉我独醒”,“悲莫悲兮”国将逝。
全诗以4言为主,兼有3言、5言、6言,句式随抒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,灵活自若,伸缩有度,极尽腾挪之事,活波而且自由,读来颇有参差排宕之美。故而,余冠英先生说:“本篇虚字多,句法参差,形式上有其特点。”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赞美该诗的艺术情势:“诗如行文,极纵横排宕之致。”明孙鑛《批评诗经》说本诗:“只一忧字,辗转演出将十句,经中亦罕有。余文多,正意少。”这些说法,各自从不同方面,点出了本诗的一些艺术特点,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。最后,笔者要强调一点,诗歌每章章首二句,不只起到“兴”的作用。它还暗含有比喻的意思,告诫人们,有桃(棘)方能果腹,园中无桃(棘)以后,何处寻食?!这里的桃与棘,不只是简单的果品食品,他暗示着老百姓的人心向背,隐喻着施政者施政的成果和施政的对象(老百姓)。意思是,魏国统治团体离心离德,施政乏术,老百姓纷纭远避他处,寻觅乐土。如此下去,国何以存?这些,正是作者(或说诗中抒怀主人公)所深深忧愁的东西。基于此,他吞吐含蕴,长歌当哭。欲以此诗警省众人及统治者,让他们尽早自立自强,恢复国计民生。改变魏国屡被侵削,地脊民贫,缺少财力的危险处境。否则,即便是像作者这样的爱国仁人,也可能“聊以行国”,大隐于世,自守其志,明哲保身。由于,在他的内心里面,不只苦闷、失望,更是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“忧患”情节。
[赏析3]
园子里有桃,鲜红的桃子可做美肴佳品;园子里有枣,香甜的大枣可以让人充饥。而我是个甚么呢?学富五车一身才德却无人问津。难道我连桃子枣子都不如吗?才华得不到发挥的悲忿之情由此而发,忧国忧民的愁闷由此而吐。作者在直抒胸怀,反复吟唱未遇知音的愁苦心情,和耿耿于怀没法排解的忧愤以后,无可奈何地作出了“何不也远远抛开不去想”的决定。其实,他嘴上说“勿思”,恰恰说明其内心并不能“勿思”,反而愈见其忧思之深。全诗腔调低沉,与诗人内心愁肠百结、欲罢不能的痛苦与矛盾十分契合。本诗较早地刻画了中国文人忧国伤时、明珠暗投的失意形象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型。
人不但需要群居,更需要心灵的沟通。因不被理解而生感概,由感概而作歌诗,以此来表白自己的清正高洁,抒发心中的不平和愁闷,这是书生们常有的心态和做法。这类心态和做法是容易被理解的,不容易被人所理解的是,世间为何难以寻求到理解呢?人们常常看重的仅仅就是理解而已,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欲望,为何就寻觅不到?
其实,理解的难以寻觅也是容易理解的。人们各自从各自的立场去看问题,各自
北京白癜风哪家医院看的好白淀疯